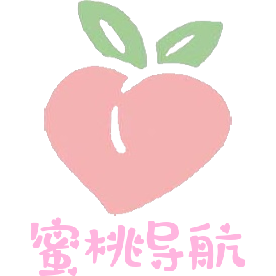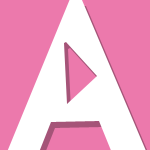站长推荐
星空入口
帝王会所
蜜桃导航
黑料福利网
吃瓜黑料网
第一导航
萝莉岛VIP
暗夜入口
狼友福利网
猛男研究所
黑料概念站
欲女自慰馆
万色广场
外网禁区
小嫂嫂导航
51福利网
TikTok入口
熟女超市
秘密研究所
全球福利汇
乱伦偷拍网
福利淫地
91福利社
初一小萝莉
换妻会所
中文情色网
三千佳丽
B站入口
隐秘部落
色色研究所
热门搜索
站长推荐
六朝清羽记 第十四集 第六章
第六章 闭月
与诸人又喝了几杯,程宗扬离席出来透透风。秦桧寸步不离跟在他身后,吴三桂正在门外,这时上前道∶「已经和石家的护卫说了,让他们先不要动手。在下按照公子的吩咐,留了张名刺。」
程宗扬点了点头。用杀人来敬酒,这些人也真做得出来。无论是石家还是王处仲都一副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样子。谢万石等人空自把德性说得嘴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程宗扬实在看不过眼,才出面解围。
王处仲的事程宗扬听着耳熟,但想不起是谁。不过既然是领过兵的,对武器兵刃总是留心的多,一试之下果然投其所好。他刚才让秦桧在席间献锥,已经先一步让吴三桂去阻拦石超的护卫。这会儿自己帮了石超一个大忙,让他饶了那两个敬酒的侍女,这点面子总会给的。
程宗扬左右张望,秦桧在旁立即道∶「那边围着锦幛的就是溷厕。」
程宗扬笑道∶「会之,你比我肚子里的蛔虫还明白。」
秦桧垂手道∶「这点察颜观色的本事,我们做手下的总要有几分。」
海蜃楼外靠近院墙的位置,一片紫色的锦幛重重叠叠围着,便是供宾客使用的厕所。云家人细心,把入口设在远离海蜃楼的另一侧,免得冲撞客人。
程宗扬绕过锦幛,正在找厕所入口,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谢家、桓家、袁家,还有张侯爷和小侯爷。」
接着一个带着金玉般清音的女声冷冷道∶「一群酒囊饭袋!」
刚才说话的婢妇道∶「大小姐,五爷说,你只要去打个照面就成。再过一会儿,那些人喝醉就不好来了。」
程宗扬一肚子的酒都变成冷汗流了出来。自己一路小心翼翼带着秦、吴二人,偏偏上个厕所就撞上这位云家大小姐。虽然自己也是客人,但这位大小姐似乎对这边的客人没什么好感。说不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狭路相逢,顺手给自己来个手起刀落,那就冤枉了。
逃进厕所也许是个好主意,可这云家的厕所也太华丽了,只看到锦幛重重,硬是找不到入口。程宗扬急中生智,那锦幛是软的,不好借力,干脆攀住院墙,一个虎跃跳了过去。
「谁!」
不等程宗扬暗自庆幸自己反应够快,云丹琉的声音便从身后响起。程宗扬低着头,施出踏雪无痕的轻功,贴着院墙一溜疾跑,钻进一个月洞门里,再腾身跃出丈许,脚尖在地上轻轻一点,同时挥袖拂去足印。
这一连串动作干净俐落,如果让殇侯看到肯定赞他修为大有精进。但程宗扬还嫌离得不够远,瞧着旁边一个院子大门紧锁,立即纵身越过院墙,一溜烟钻到院中一幢小楼里,藏好身形。
程宗扬抹了把冷汗,心里怦怦直跳。竟然被一个丫头片子吓成这样,小紫知道肯定笑死。
等了片刻没有听到外面动静,程宗扬才松了口气。这里离海蜃楼已经隔了两个院子,危险程度大大降低。云丹琉这会儿是去楼中会客,程宗扬打定主意就在这里躲半个时辰,等她走了再回去。
刚才被吓了一跳,此时心神一松,尿意更显急迫。程宗扬进来时留心看过,这个院子虽然干净,但大门紧锁像是没人住。楼前种着一池花草、几竿修竹,幽静雅致。
程宗扬不敢离开小楼,索性就在楼门口拉开裤子,对着楼前的花池痛痛快快地方便起来。
大概是那些酒都吓了出来,这泡尿分外长,程宗扬一边尿一边左右打量这座小楼。
院中像是时常有人打扫,青砖铺成的地上片尘不染。门内两侧各摆着一只一人多高的大花瓶,白瓷的瓶身上绘着踏雪寻梅。画中一个少女穿着大红的氅衣,纤手攀着一枝红梅正在轻嗅。
在她旁边,一张雪白的面孔掩在毛茸茸的狐裘中,春水般的美眸怯生生看着自己。
程宗扬一手提着裤子,正「哗哗」地尿得痛快。忽然间浑身打了个寒颤,猛地回过头。
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卓云君打了个冷颤,咳嗽着醒来。
那妇人站在她面前,虽然脸上涂着厚粉,仍能看出她脸色不善,阴沉得彷佛要下起暴雨。
这几日卓云君在她手下吃了无数苦头,看到她的神情心下先自怯了,禁不住身子微微发抖。
那妇人沙哑着喉咙道∶「想死?」
说着她抬脚踩住卓云君的手指,又问了一遍∶「是不是想死?」
那妇人穿着一双木屐,屐齿踩在卓云君修长的玉指上,用力一拧。
十指连心,卓云君身体一颤,脸色一瞬间变得灰白,接着发出一声凄叫;叫声透过门窗被外面厚厚的被褥吸收,在外面听来就和小猫的哀鸣差不多。手指的骨骼彷佛寸寸碎裂,与血肉碎成一团,痛得卓云君浑身都渗出冷汗。
凄叫声中,妇人骂道∶「不要脸的臭娼妇!这么便宜就想死?」
卓云君只觉手指在她屐齿下格格作响,正一根根在她脚下断裂。她本身是用剑的高手,对手指分外关心;剧痛和恐惧潮水般涌上心头,卓云君不由失声道∶「求你不要踩了!不要踩了!」
「哟,道姑奶奶在讨饶呢。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那妇人嘲讽着,脚下没有丝毫放松,反而用力一拧。卓云君手指彷佛尽数碎裂,破碎的指骨刺进血肉。卓云君呼吸一窒,瞳孔放大,正痛得要昏迷过去,那妇人木屐忽然一松,接着又再次用力。
卓云君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尖叫,身子像触电一样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妇人似乎摸准了她的感受,每次她接近昏厥的时候都略微放松,等她喘过气,再加倍用力,使她始终处于能忍受的剧痛之中。
卓云君散乱的发丝被汗水打湿,一缕缕贴在苍白的脸上。她用了不知多久时间才终于挣开腕上的麻绳。卓云君本来想趁机逃走,可她脚上的麻绳打了两个死结,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解开。
心灰意冷下,卓云君在麻绳系在桌子下面打了个结,采取自缢的方式来脱离这种绝望的境地。可她伏在地上,身体并没有悬空,自缢的过程分外漫长,刚昏迷过去就被人救起。
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卓云君心防已破,剧痛下更是风度尽失。她双手被木屐踩住,痛得凄声惨叫,一边哀求讨饶。
「浪蹄子!你不是想死吗?」
那妇人恶狠狠说着,拿起麻绳绕在卓云君昂起的颈上,用力一绞。
卓云君正尖声惨叫,被麻绳一勒,顿时呼吸断绝,惨叫声噎在喉中。粗糙的麻绳在颈中磨擦着绞紧,彷佛将生命一点一点挤出体外。
卓云君双手仍被木屐踩住,玉颈昂起,强烈的窒息感使她眼睛充血,被勒得凸起,肺部像要爆炸一样剧痛,身体每一丝肌肉都在痉挛。她神智变得恍惚,瞳孔因为死亡的逼近,一点点扩大。
卓云君曾经尝试过自尽,但当死亡真来临的一刻,她却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恐惧。她拼命伸长颈子,竭尽全力呼吸着,此刻只要能吸进一丝空气,她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换,只要能够活下去、摆脱死亡的痛楚。
忽然,麻绳一松,空气涌入火辣辣的肺中。卓云君颤抖着,已经模糊的视野渐渐变得清晰。
「死娼妇!还想不想死!」
那妇人一声厉喝,使卓云君打了个咚嗦。她无力地摇了摇头,脸上曾经的高傲和英气荡然无存,就像一个陷入绝境的平常女人一样崩溃了。
那妇人骂道∶「老娘好心好意养着你,竟然想死?己她一手挽着麻绳,一手抓住卓云君的头发,把她面孔按在沾满饭粒的地上,吵哑着声音威胁道∶「舔干净!」
卓云君颤抖片刻,然后张开嘴,用苍白的唇舌含住那些已经泼出来一整天的饭粒。
如果可能,她宁肯自绝心脉,也不愿在这地狱般的黑暗多活一刻,但自己甚至连死亡的自由也没有。绞颈的痛楚摧毁了她的意志,既然连死亡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骄傲如卓云君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卓云君屈辱地含住饭粒,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妇人木屐一紧,卓云君惨叫声中,脖颈又被麻绳勒住。刚才可怕的经历使卓云君刻骨难忘,不等麻绳勒紧,她就拼命摇头,然后俯身一口一口把饭粒舔干净。
「贱货!老娘好言好语你当成耳边风,非要挨打才听话!」
那妇人抄起门闩朝卓云君一通痛打,最后把麻绳往她脸上一丢∶「你想死就接着死!吊死了就拖出去喂狗!」
卓云君脸色灰白,双手一阵一阵痉挛,身体不住咚嗦。她散乱的目光掠过地上的麻绳,就像看到一条毒蛇一样,露出无比的惧意。
程宗扬张大嘴巴,看着花瓶旁一个裹着狐裘的小美人儿。现在正值八月,天气刚刚开始转凉,她却穿着厚厚的狐裘,一张精致的小脸白得彷佛透明,眉毛弯弯的,纤秀如画。难怪自己刚才把她当成瓶上画的美女。
程宗扬脱口道∶「你是谁?」
那少女粉颊微红,细声道∶「你……是谁?」
程宗扬原以为这里没人,又怕撞上云丹琉,才大模大样站在楼门口方便。谁知道会被这个精致如画的小美人儿碰个正着。这会儿自己刚尿了一半,想收也收不住,索性厚起脸皮,哗哗尿完再说。
少女晕生双颊,鼓足勇气道∶「那是我的兰花……」
程宗扬厚着脸皮移了移位置,避开那些兰花。
那少女像是快哭了一样小声道∶「那是我的竹子……」
「……施了肥才长得更旺啊。」
程宗扬开始有点佩服自己,脸皮竟然这么厚,在别人家门口随地小便,被女主人撞上还能脸不红心不跳。
「咦?谁挖的小沟?还放着几个小泥人?」
「……那是竹林诸贤和曲水流觞。」
竹林诸贤是魏晋风流的开山人物,曲水流觞刚才程宗扬在席间听了不少。晋国文人聚会时,常在溪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羽觞放在水中顺流而下。羽觞在谁面前打转或者停下,谁就举觞畅饮、即兴赋诗,是一等一的风流雅事。
那几竿翠竹间被人细心地挖出一条小溪,溪旁坐着竹林诸贤的小泥人,溪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带耳羽觞。这会儿羽觞也浮了起来,但怎么浮起来的,就不必再说了。
程宗扬狠狠打了个尿颤,一身畅快地提上裤子,这才转过身,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在下姓萧,萧遥逸。萧某去也。」
程宗扬回身就跑,便听到云丹琉的声音∶「门怎么锁了?还不打开!」
程宗扬立刻窜了回来,他也不敢开口,双手合十朝那少女拜了几拜,就一头钻进楼里。
「大小姐,瑶小姐这些日子正发寒。老爷吩咐过不让人来打扰。连汤饭都是递进去的。」
「我两年才回来一趟,就不能见见姑姑吗?」
仆妇道∶「只需过了这几日,瑶小姐每日就能见半个时辰的客。院门的钥匙在老爷手里,大小姐就是要进,我们也打不开。再说,瑶小姐的身子大小姐也知道,每月发寒的几日,我们这些下人都提着心,只怕吹口气就化了的。」
程宗扬躲进楼内,才发现这座小楼窗户都是封死的,云丹琉不进来便罢,一旦闯进来就是瓮中捉鳖,一逮一个准。
穿着狐裘的瑶小姐站在门口,静静听着外面的交谈。不知为何,程宗扬看着她的背影,心头泛起一丝凄清的落寞感。
云丹琉终于还是没有硬闯,她在外面说道∶「姑姑,丹琉给你带了些东西,让她们给你递进去。过几日姑姑身体大好,丹琉再来看你。」
程宗扬松了口气,云丹琉明明要到前面见客,不知道怎么又绕到这里。被那个丫头片子吓了两次,腿都有点不好使。程宗扬索性坐在扶手上滑下来,然后小心翼翼绕开那位瑶小姐,陪笑道∶「打扰了,萧某……」
瑶小姐慢慢抬起脸∶「我才没有那么弱……刚才我就没有昏倒……」
她秀美的面孔半掩在雪白的狐毛间,眉眼间寂寞的神情让程宗扬心头一空,升起一丝怜意。
瑶小姐低声道∶「你帮我拿来,好不好?」
「唔?」
程宗扬扭过头,才发现院门一角有个活动的门板,一只细心打理过的包裹放在门边。
「这是什么?」
程宗扬一泡尿毁了人家的竹林诸贤和曲水流觞,让萧遥逸背黑锅事小,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实在说不过去。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包裹取过来,帮那个瑶小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取出来。
看不出云丹琉还颇为细心,每件东西都用小木盒装着,淡黄的木盒是用上好的檀香木制成,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里面装的都是小孩子喜欢的贝壳、海星、小珊瑚之类的物品。
「这是鹦鹉螺。」
程宗扬道∶「装上杯耳能做成漂亮的小酒杯。」
「这个呢?是琥珀吗?」
程宗扬拿起那个透明的物体,有点不确定地说∶「是海底的琥珀吧。」
「我看书上说,琥珀是虎睛沉到地下变成的。海里也有老虎吗?」
程宗扬笑道∶「琥珀是滴下来的树脂变成的,有些里面还有小虫子。用力磨擦,能闻到松脂的香气。」
那少女悠悠叹了口气∶「那些小虫子好可怜……」
一个人孤零零待在院里,也像极了囚在琥珀中的虫子。程宗扬打开一只狭长的木盒,里面是一根白色的物体,看起来和他的龙牙锥有点像,不过更长一些,质地轻而柔软。
「这是什么?」
程宗扬试着弯了弯,那根物体极富弹性,弯成圆形也能轻易弹直,手感有点塑胶的感觉。自然界里像这样天然的弹性物体并不多见,程宗扬想了一会儿,忽然道∶「鲸须!嘿,这条鲸须快有三尺了吧,他们居然猎了这么大一条鲸!」
「是海里大鱼的胡子吗?」
程宗扬费了半天工夫,给她讲了鲸的样子和习性。那少女听得悠然神往,轻叹道∶「不知我何时才能见到那样大的鲸。」
程宗扬越来越感受到她的寂寞,自己那会儿的举止不只是唐突,把人家精心布置的曲水流觞毁了,简直粗鲁到令人发指,这个瑶小姐却没有生气,也许很久都没有外人来过与她说话了,此时对着一个陌生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程宗扬说完鲸须,又打开另外一只木盒。那木盒四四方方,里面装着一块琥珀色的不规则物体,体积约拳头大小,像一块脏兮兮的泥土,貌不惊人。
程宗扬把它拿起来惦了惦,大概有一斤多重,瞧不出是什么东西。看着瑶小姐殷切的眼神,程宗扬遗憾地想∶祁远这会儿要在,肯定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他放下那块东西,随手摸了摸鼻子,忽然闻到手指上一股异香。程宗扬心里一动,从衣下的背包中拿出火摺用力摇亮。
那东西燃点极低,火苗刚递过去,便腾起一层细微的蓝色火焰,一股浓郁的异香随即飘散开来,将整座小楼都染得香气扑鼻。
「龙涎香!」
程宗扬终于敢断定,这就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龙涎香。
云丹琉对这个瑶小姐还真好,这么大一块龙涎香,大概要价值几倍重量的黄金才能换到。
「真的好香……」
瑶小姐轻轻说了一句,然后软绵绵倒了下去。
程宗扬连忙扔下龙涎香,一把扶住她。瑶小姐脸色雪白,口鼻间只有一缕游丝般微弱的气息。
程宗扬试了试她的额头,手掌彷佛摸在雪上一样,一片冰凉。
与诸人又喝了几杯,程宗扬离席出来透透风。秦桧寸步不离跟在他身后,吴三桂正在门外,这时上前道∶「已经和石家的护卫说了,让他们先不要动手。在下按照公子的吩咐,留了张名刺。」
程宗扬点了点头。用杀人来敬酒,这些人也真做得出来。无论是石家还是王处仲都一副不把人命放在眼里的样子。谢万石等人空自把德性说得嘴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程宗扬实在看不过眼,才出面解围。
王处仲的事程宗扬听着耳熟,但想不起是谁。不过既然是领过兵的,对武器兵刃总是留心的多,一试之下果然投其所好。他刚才让秦桧在席间献锥,已经先一步让吴三桂去阻拦石超的护卫。这会儿自己帮了石超一个大忙,让他饶了那两个敬酒的侍女,这点面子总会给的。
程宗扬左右张望,秦桧在旁立即道∶「那边围着锦幛的就是溷厕。」
程宗扬笑道∶「会之,你比我肚子里的蛔虫还明白。」
秦桧垂手道∶「这点察颜观色的本事,我们做手下的总要有几分。」
海蜃楼外靠近院墙的位置,一片紫色的锦幛重重叠叠围着,便是供宾客使用的厕所。云家人细心,把入口设在远离海蜃楼的另一侧,免得冲撞客人。
程宗扬绕过锦幛,正在找厕所入口,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谢家、桓家、袁家,还有张侯爷和小侯爷。」
接着一个带着金玉般清音的女声冷冷道∶「一群酒囊饭袋!」
刚才说话的婢妇道∶「大小姐,五爷说,你只要去打个照面就成。再过一会儿,那些人喝醉就不好来了。」
程宗扬一肚子的酒都变成冷汗流了出来。自己一路小心翼翼带着秦、吴二人,偏偏上个厕所就撞上这位云家大小姐。虽然自己也是客人,但这位大小姐似乎对这边的客人没什么好感。说不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此时狭路相逢,顺手给自己来个手起刀落,那就冤枉了。
逃进厕所也许是个好主意,可这云家的厕所也太华丽了,只看到锦幛重重,硬是找不到入口。程宗扬急中生智,那锦幛是软的,不好借力,干脆攀住院墙,一个虎跃跳了过去。
「谁!」
不等程宗扬暗自庆幸自己反应够快,云丹琉的声音便从身后响起。程宗扬低着头,施出踏雪无痕的轻功,贴着院墙一溜疾跑,钻进一个月洞门里,再腾身跃出丈许,脚尖在地上轻轻一点,同时挥袖拂去足印。
这一连串动作干净俐落,如果让殇侯看到肯定赞他修为大有精进。但程宗扬还嫌离得不够远,瞧着旁边一个院子大门紧锁,立即纵身越过院墙,一溜烟钻到院中一幢小楼里,藏好身形。
程宗扬抹了把冷汗,心里怦怦直跳。竟然被一个丫头片子吓成这样,小紫知道肯定笑死。
等了片刻没有听到外面动静,程宗扬才松了口气。这里离海蜃楼已经隔了两个院子,危险程度大大降低。云丹琉这会儿是去楼中会客,程宗扬打定主意就在这里躲半个时辰,等她走了再回去。
刚才被吓了一跳,此时心神一松,尿意更显急迫。程宗扬进来时留心看过,这个院子虽然干净,但大门紧锁像是没人住。楼前种着一池花草、几竿修竹,幽静雅致。
程宗扬不敢离开小楼,索性就在楼门口拉开裤子,对着楼前的花池痛痛快快地方便起来。
大概是那些酒都吓了出来,这泡尿分外长,程宗扬一边尿一边左右打量这座小楼。
院中像是时常有人打扫,青砖铺成的地上片尘不染。门内两侧各摆着一只一人多高的大花瓶,白瓷的瓶身上绘着踏雪寻梅。画中一个少女穿着大红的氅衣,纤手攀着一枝红梅正在轻嗅。
在她旁边,一张雪白的面孔掩在毛茸茸的狐裘中,春水般的美眸怯生生看着自己。
程宗扬一手提着裤子,正「哗哗」地尿得痛快。忽然间浑身打了个寒颤,猛地回过头。
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卓云君打了个冷颤,咳嗽着醒来。
那妇人站在她面前,虽然脸上涂着厚粉,仍能看出她脸色不善,阴沉得彷佛要下起暴雨。
这几日卓云君在她手下吃了无数苦头,看到她的神情心下先自怯了,禁不住身子微微发抖。
那妇人沙哑着喉咙道∶「想死?」
说着她抬脚踩住卓云君的手指,又问了一遍∶「是不是想死?」
那妇人穿着一双木屐,屐齿踩在卓云君修长的玉指上,用力一拧。
十指连心,卓云君身体一颤,脸色一瞬间变得灰白,接着发出一声凄叫;叫声透过门窗被外面厚厚的被褥吸收,在外面听来就和小猫的哀鸣差不多。手指的骨骼彷佛寸寸碎裂,与血肉碎成一团,痛得卓云君浑身都渗出冷汗。
凄叫声中,妇人骂道∶「不要脸的臭娼妇!这么便宜就想死?」
卓云君只觉手指在她屐齿下格格作响,正一根根在她脚下断裂。她本身是用剑的高手,对手指分外关心;剧痛和恐惧潮水般涌上心头,卓云君不由失声道∶「求你不要踩了!不要踩了!」
「哟,道姑奶奶在讨饶呢。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那妇人嘲讽着,脚下没有丝毫放松,反而用力一拧。卓云君手指彷佛尽数碎裂,破碎的指骨刺进血肉。卓云君呼吸一窒,瞳孔放大,正痛得要昏迷过去,那妇人木屐忽然一松,接着又再次用力。
卓云君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尖叫,身子像触电一样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妇人似乎摸准了她的感受,每次她接近昏厥的时候都略微放松,等她喘过气,再加倍用力,使她始终处于能忍受的剧痛之中。
卓云君散乱的发丝被汗水打湿,一缕缕贴在苍白的脸上。她用了不知多久时间才终于挣开腕上的麻绳。卓云君本来想趁机逃走,可她脚上的麻绳打了两个死结,无论怎么用力都无法解开。
心灰意冷下,卓云君在麻绳系在桌子下面打了个结,采取自缢的方式来脱离这种绝望的境地。可她伏在地上,身体并没有悬空,自缢的过程分外漫长,刚昏迷过去就被人救起。
从死亡边缘回来的卓云君心防已破,剧痛下更是风度尽失。她双手被木屐踩住,痛得凄声惨叫,一边哀求讨饶。
「浪蹄子!你不是想死吗?」
那妇人恶狠狠说着,拿起麻绳绕在卓云君昂起的颈上,用力一绞。
卓云君正尖声惨叫,被麻绳一勒,顿时呼吸断绝,惨叫声噎在喉中。粗糙的麻绳在颈中磨擦着绞紧,彷佛将生命一点一点挤出体外。
卓云君双手仍被木屐踩住,玉颈昂起,强烈的窒息感使她眼睛充血,被勒得凸起,肺部像要爆炸一样剧痛,身体每一丝肌肉都在痉挛。她神智变得恍惚,瞳孔因为死亡的逼近,一点点扩大。
卓云君曾经尝试过自尽,但当死亡真来临的一刻,她却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恐惧。她拼命伸长颈子,竭尽全力呼吸着,此刻只要能吸进一丝空气,她愿意用自己的一切来换,只要能够活下去、摆脱死亡的痛楚。
忽然,麻绳一松,空气涌入火辣辣的肺中。卓云君颤抖着,已经模糊的视野渐渐变得清晰。
「死娼妇!还想不想死!」
那妇人一声厉喝,使卓云君打了个咚嗦。她无力地摇了摇头,脸上曾经的高傲和英气荡然无存,就像一个陷入绝境的平常女人一样崩溃了。
那妇人骂道∶「老娘好心好意养着你,竟然想死?己她一手挽着麻绳,一手抓住卓云君的头发,把她面孔按在沾满饭粒的地上,吵哑着声音威胁道∶「舔干净!」
卓云君颤抖片刻,然后张开嘴,用苍白的唇舌含住那些已经泼出来一整天的饭粒。
如果可能,她宁肯自绝心脉,也不愿在这地狱般的黑暗多活一刻,但自己甚至连死亡的自由也没有。绞颈的痛楚摧毁了她的意志,既然连死亡都是无法企及的奢望,骄傲如卓云君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卓云君屈辱地含住饭粒,却怎么也咽不下去。
那妇人木屐一紧,卓云君惨叫声中,脖颈又被麻绳勒住。刚才可怕的经历使卓云君刻骨难忘,不等麻绳勒紧,她就拼命摇头,然后俯身一口一口把饭粒舔干净。
「贱货!老娘好言好语你当成耳边风,非要挨打才听话!」
那妇人抄起门闩朝卓云君一通痛打,最后把麻绳往她脸上一丢∶「你想死就接着死!吊死了就拖出去喂狗!」
卓云君脸色灰白,双手一阵一阵痉挛,身体不住咚嗦。她散乱的目光掠过地上的麻绳,就像看到一条毒蛇一样,露出无比的惧意。
程宗扬张大嘴巴,看着花瓶旁一个裹着狐裘的小美人儿。现在正值八月,天气刚刚开始转凉,她却穿着厚厚的狐裘,一张精致的小脸白得彷佛透明,眉毛弯弯的,纤秀如画。难怪自己刚才把她当成瓶上画的美女。
程宗扬脱口道∶「你是谁?」
那少女粉颊微红,细声道∶「你……是谁?」
程宗扬原以为这里没人,又怕撞上云丹琉,才大模大样站在楼门口方便。谁知道会被这个精致如画的小美人儿碰个正着。这会儿自己刚尿了一半,想收也收不住,索性厚起脸皮,哗哗尿完再说。
少女晕生双颊,鼓足勇气道∶「那是我的兰花……」
程宗扬厚着脸皮移了移位置,避开那些兰花。
那少女像是快哭了一样小声道∶「那是我的竹子……」
「……施了肥才长得更旺啊。」
程宗扬开始有点佩服自己,脸皮竟然这么厚,在别人家门口随地小便,被女主人撞上还能脸不红心不跳。
「咦?谁挖的小沟?还放着几个小泥人?」
「……那是竹林诸贤和曲水流觞。」
竹林诸贤是魏晋风流的开山人物,曲水流觞刚才程宗扬在席间听了不少。晋国文人聚会时,常在溪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羽觞放在水中顺流而下。羽觞在谁面前打转或者停下,谁就举觞畅饮、即兴赋诗,是一等一的风流雅事。
那几竿翠竹间被人细心地挖出一条小溪,溪旁坐着竹林诸贤的小泥人,溪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带耳羽觞。这会儿羽觞也浮了起来,但怎么浮起来的,就不必再说了。
程宗扬狠狠打了个尿颤,一身畅快地提上裤子,这才转过身,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在下姓萧,萧遥逸。萧某去也。」
程宗扬回身就跑,便听到云丹琉的声音∶「门怎么锁了?还不打开!」
程宗扬立刻窜了回来,他也不敢开口,双手合十朝那少女拜了几拜,就一头钻进楼里。
「大小姐,瑶小姐这些日子正发寒。老爷吩咐过不让人来打扰。连汤饭都是递进去的。」
「我两年才回来一趟,就不能见见姑姑吗?」
仆妇道∶「只需过了这几日,瑶小姐每日就能见半个时辰的客。院门的钥匙在老爷手里,大小姐就是要进,我们也打不开。再说,瑶小姐的身子大小姐也知道,每月发寒的几日,我们这些下人都提着心,只怕吹口气就化了的。」
程宗扬躲进楼内,才发现这座小楼窗户都是封死的,云丹琉不进来便罢,一旦闯进来就是瓮中捉鳖,一逮一个准。
穿着狐裘的瑶小姐站在门口,静静听着外面的交谈。不知为何,程宗扬看着她的背影,心头泛起一丝凄清的落寞感。
云丹琉终于还是没有硬闯,她在外面说道∶「姑姑,丹琉给你带了些东西,让她们给你递进去。过几日姑姑身体大好,丹琉再来看你。」
程宗扬松了口气,云丹琉明明要到前面见客,不知道怎么又绕到这里。被那个丫头片子吓了两次,腿都有点不好使。程宗扬索性坐在扶手上滑下来,然后小心翼翼绕开那位瑶小姐,陪笑道∶「打扰了,萧某……」
瑶小姐慢慢抬起脸∶「我才没有那么弱……刚才我就没有昏倒……」
她秀美的面孔半掩在雪白的狐毛间,眉眼间寂寞的神情让程宗扬心头一空,升起一丝怜意。
瑶小姐低声道∶「你帮我拿来,好不好?」
「唔?」
程宗扬扭过头,才发现院门一角有个活动的门板,一只细心打理过的包裹放在门边。
「这是什么?」
程宗扬一泡尿毁了人家的竹林诸贤和曲水流觞,让萧遥逸背黑锅事小,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人实在说不过去。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包裹取过来,帮那个瑶小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取出来。
看不出云丹琉还颇为细心,每件东西都用小木盒装着,淡黄的木盒是用上好的檀香木制成,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里面装的都是小孩子喜欢的贝壳、海星、小珊瑚之类的物品。
「这是鹦鹉螺。」
程宗扬道∶「装上杯耳能做成漂亮的小酒杯。」
「这个呢?是琥珀吗?」
程宗扬拿起那个透明的物体,有点不确定地说∶「是海底的琥珀吧。」
「我看书上说,琥珀是虎睛沉到地下变成的。海里也有老虎吗?」
程宗扬笑道∶「琥珀是滴下来的树脂变成的,有些里面还有小虫子。用力磨擦,能闻到松脂的香气。」
那少女悠悠叹了口气∶「那些小虫子好可怜……」
一个人孤零零待在院里,也像极了囚在琥珀中的虫子。程宗扬打开一只狭长的木盒,里面是一根白色的物体,看起来和他的龙牙锥有点像,不过更长一些,质地轻而柔软。
「这是什么?」
程宗扬试着弯了弯,那根物体极富弹性,弯成圆形也能轻易弹直,手感有点塑胶的感觉。自然界里像这样天然的弹性物体并不多见,程宗扬想了一会儿,忽然道∶「鲸须!嘿,这条鲸须快有三尺了吧,他们居然猎了这么大一条鲸!」
「是海里大鱼的胡子吗?」
程宗扬费了半天工夫,给她讲了鲸的样子和习性。那少女听得悠然神往,轻叹道∶「不知我何时才能见到那样大的鲸。」
程宗扬越来越感受到她的寂寞,自己那会儿的举止不只是唐突,把人家精心布置的曲水流觞毁了,简直粗鲁到令人发指,这个瑶小姐却没有生气,也许很久都没有外人来过与她说话了,此时对着一个陌生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程宗扬说完鲸须,又打开另外一只木盒。那木盒四四方方,里面装着一块琥珀色的不规则物体,体积约拳头大小,像一块脏兮兮的泥土,貌不惊人。
程宗扬把它拿起来惦了惦,大概有一斤多重,瞧不出是什么东西。看着瑶小姐殷切的眼神,程宗扬遗憾地想∶祁远这会儿要在,肯定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他放下那块东西,随手摸了摸鼻子,忽然闻到手指上一股异香。程宗扬心里一动,从衣下的背包中拿出火摺用力摇亮。
那东西燃点极低,火苗刚递过去,便腾起一层细微的蓝色火焰,一股浓郁的异香随即飘散开来,将整座小楼都染得香气扑鼻。
「龙涎香!」
程宗扬终于敢断定,这就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龙涎香。
云丹琉对这个瑶小姐还真好,这么大一块龙涎香,大概要价值几倍重量的黄金才能换到。
「真的好香……」
瑶小姐轻轻说了一句,然后软绵绵倒了下去。
程宗扬连忙扔下龙涎香,一把扶住她。瑶小姐脸色雪白,口鼻间只有一缕游丝般微弱的气息。
程宗扬试了试她的额头,手掌彷佛摸在雪上一样,一片冰凉。